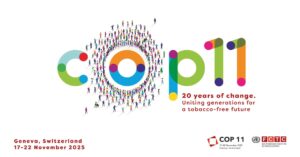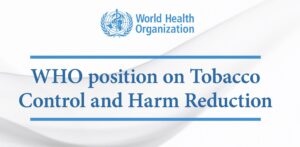劉成謙觀點:預算不能成為政治表演的舞台 從美國政府停擺看台灣預算僵局的制度反思

文/劉成謙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學生
2019年冬天,美國聯邦政府陷入長達35天的停擺,創下史上最久紀錄。因時任但也是現在的美國總統川普,在其2016年競選時曾承諾,將在美墨邊境修築「邊境牆」,以杜絕邊境非法移民以及毒品走私。2018年,川普開始推動相關的計畫,但在年底這項支出遭到國會拒絕,川普也旋即表示,他不會簽署不含美墨邊境牆的預算,陷入預算僵局。該年12月19日,參議院通過了2019年的繼續撥款法,使撥款能一直持續到2019年2月8日。但是川普在第二天宣布他不會簽署不含美墨築牆經費的臨時支出法案。總之,參眾兩院以及總統的三方分岐,導致聯邦政府在12月22日開始因沒有預算停擺,直至2019年1月25日,川普同意重新開放政府三周。
美國聯邦政府停擺會怎樣?
聯邦政府關閉引發的衝擊,區分為必要服務和非必要服務,部分聯邦公務員會放無薪假,總體上約有40%的聯邦政府僱員被迫休假,比如環境、教育、商務、住房等部門的多數政府公務員。
某些項目並不會停止,大致上有公共安全、邊境保護、軍隊武裝、電網維護、執法、立法、司法等服務。而另外,有些州和地方政府,需要依靠聯邦政府負擔部分資金,所以會受到一定的影響。美國民眾從被關停部門的感受到的衝擊,除了需要依靠聯邦資金的州和地方政府外,其他比如航空交通堵塞和航班延誤、國稅局退稅服務的延遲、在首都華盛頓,可能出現垃圾無人清掃、堆積如山的場景、向政府申請的貸款審批時間延長、軍人收到的是工資欠條,而非支票、停擺期間國家公園、國家動物園、國立博物館關閉,及聯邦煙、酒、火器和爆炸品管制局的工作停滯導致購槍證延遲等等。
反思台美預算僵局的情況與處理機制
關於美國聯邦預算不成立的處理機制:國會通過替代的繼續撥款法案(continuing appropriations),總統簽署可維持聯邦政府繼續運作一段時間,雙邊協商試圖化解僵局。
而台灣則是依預算法第54條規定,總預算案之審議,如不能依第五十一條期限(會計年度開始一個月前由立法院議決) 完成時,各機關預算之執行,依下列規定為之:收入部分暫依上年度標準及實際發生數,覈實收入。支出部分:(一)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計畫,須俟本年度預算完成審議程序後始得動支。但依第八十八條規定辦理或經立法院同意者,不在此限。(二)前目以外計畫得依已獲授權之原訂計畫或上年度執行數,覈實動支。履行其他法定義務收支。因應前三款收支調度需要之債務舉借,覈實辦理。
簡而言之,就是當我國會預算案無法通過時,為了避免政府停擺,會依照前一年度的收入與支出繼續維持政府的運行,是為「暫行編列」。
今年度,美國一樣陷入預算僵局,但是與2019年僵局不同的是,因為適逢執政黨轉換,前任總統民主黨的拜登在卸任前,於2024年12月通過了臨時撥款法案,讓政府得以運行至今年的3月,3月到4月間的政府則是靠著財政部的非常規措施,美國財政部動用了現金儲備,來撐過這一段時期。
更細節的來談美國預算僵局,美國的政府預算需經由國會兩院(眾議院與參議院)通過,最後由總統簽署。所以才會有2018-2019年政府停擺的情況,當初的情況是為了興建美墨邊境牆的經費來源所引發的衝突,如果國會通過的預算案沒有加上美墨邊境牆的預算,川普就不簽署其他法案。但其實這些年來,美國預算僵局的情況越來越常發生,2018年、2021年、2023年以及前述的2024年的預算案皆發生僵局,而美國預算案僵局的不斷發生,基本上會是政治上的分歧導致的,不論是美國的民主黨及共和黨兩黨對立愈來愈嚴重,或是全球極右翼興起的情況下,美國也不可避免的在右翼政黨內形成了極右翼集團,近一步造成政治上的分裂,或是預算案成為爭議法案的舞台,預算審議成為政治對抗的中心,這些都是原因之一。另外,全世界的民主國家,如法國、韓國與德國,也都或多或少都面臨到前述的這些問題而動盪著。
今年的美國預算案的焦點在,共和黨推動削減政府開支、高達 5.3 兆美元的減稅計畫及 5 兆美元的債限調升鋪平道路,川普的第二輪稅改將延續其任期內已施行的減稅政策,並新增優惠措施,包括擴大州與地方稅抵扣、取消對小費工資的課稅等。
總之,連年的預算僵局、連年險之又險的繼續撥款法案,如果我是美國公民,不得不令人思考現在制度的合理性,雖然說美國是聯邦制,在聯邦政府停擺的情況下,還有州政府跟地方政府在運行,但對於向聯邦政府申請業務的民眾,還有美國在經濟上的信心都有不小的影響,當然對於許多聯邦公務員以及軍人來講,更是困擾且不公,因此我會認為,單就這部分,其實可以參考台灣的延續上一年度的預算這個模式,來維持住聯邦政府的運作;當然,放到總體來看我並不覺得這樣子是最好,這可能有損美國發展已久的政治系統,比如說當政府遇到預算僵局以及政府關門時,民眾會透過這樣的事件來了解原因,再去檢視國會以及聯邦政府的立場,可能可以決定比如說遊說的立場、期中選舉的選擇,可以將其理解為政治上的市場自由的概念,或者說是由經濟上演變過來的價值,政府不需要對市場過多的干預,因此就算政府停擺也無所謂,也有有限政府以及最小政府的思維在裡面。但如果真的要談,我覺得這可以是階段性的作法,例如選舉年,預算的僵局就更可能發生,因此需要使用這套系統,以避免純政治對抗下的預算僵局,讓預算成為政治表演的舞台,這樣的情況真正受害的是人民。
回頭看看台灣,中華民國是單一制國家,不同於美國,因此,若是預算案發生僵局,政府一停擺,可沒有州政府來幫忙,而且,根據我們地方政府的情況,很仰賴中央的統籌分配稅款,政治定位上也差很多。如此一來,連地方政府都要幾近癱瘓,這樣一看,暫行編列真的是很好的做法,有效因應了因為各種因素僵持的中央預算案,維持住政府的持續運行。
台灣預算僵局的真正問題在此
所以我們自身比較大的問題,應該是來自於政治系統,當然我們的預算也經常錯過會計年度,但在暫行編列的效果之下,國民是相當無感的,甚至我記得在當年,就是川普的第一個任期發生的這個2018-2019聯邦政府停擺,我及身邊的所有人想像都是以中華民國政府的狀況去思考的,也就是認為說一旦聯邦政府停擺,很多的政府機能都會消失,所以當我國去年末及今年初在討論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僵局時,多數人的想像是中華民國政府也會像美國一樣完全停擺,進而變成在質疑在野黨是否想要癱瘓國家,不是去檢討執政黨協商不利,忘掉「政治是妥協的藝術」這句話。多數民眾並不知道「暫行編列」的機制,而預算這門政府重要的課題,也在公眾輿論之下消失很久,也才會有人相信統一發票獎金是可以被刪除的預算。
這背後的一大隱憂是責任政治的消逝,過往當預算僵局時、朝小野大時,執政的政府通常會願意放下身段來與在野黨妥協,謀求執政順利,以推行它們的政策,且因為預算陷入僵局施政不利時,民眾會將責任歸咎於執政黨使其概括承受,這會影響到的是接續執政的選舉或是期中選舉的地方選舉。但當民眾開始檢討在野黨時,彷彿監督預算內容是一種罪行,這違背立法委員本身的職權,當然本屆國會與今年度預算案被刪減及凍結的內容都還需要再討論。
再者是連續不斷的總預算案覆議案,如果中央政府總預算無法通過全是在野黨的責任,那前述講的這種執政團隊應背負的政治責任就消失了;也難怪閣揆可以不斷的將總預算再送回立法院覆議,雖然這是攸關國家的大事,一般來說這是會代表人民對執政團隊能否帶領國家向前行的信心關鍵因素之一,但我們的政府首腦並沒有去負任何政治責任,且貌似民眾、執政黨支持者對此都沒有任何感覺。
另外,在我們的政府機制當中,閣揆與總統也沒有辦法去處理如此預算僵局的情況,沒有任何憲政權力,不像日英兩國內閣制的首相能提請王室解散議會,也不像法國的半總統制之總統能夠去解散國會;有些國家在預算僵局時,不成文的規定閣揆會下台以示負責,或者是在憲政系統之下總理需要自行請辭,而這些都會讓閣揆與國會有代價有顧忌地去面對預算的僵局,畢竟這些都會影響給他們政治正當性的人民的生活;所以,我們的政府機制既然是沒有處理這塊的憲政權力,僅依靠預算法在維持的話,那我們就需要去建立出一個當預算僵局時的憲政慣例,否則每一個閣揆遇到預算僵局時就是不斷的去送總預算案的覆議案,且在機制上也沒有限制,那他就可以無限地去送覆議案,甚至使其變成是一種政治工具,這不就是鑽系統的漏洞嗎?(當然,這項政治工具討好到的也包含另一方的支持者,在政治激烈表演預算持續僵局的情況,受害的會是人民,所以國會也有其自己角色的責任要負。)
總之,關於責任政治的觀念建立非常重要,不僅是靠我們的政府機制或公民素養其一,而是需要兩者兼備相互影響制衡。我們的公民教育要傳達的內容,公民才是國家的主人,如果公民不能有效的監督國家政府的運作,淪為政黨所煽動對象之一,就無法有效的限制國家權力的擴張。公民社會要能夠真正的監督政府,促成一個真正的有限政府,避免不了在野黨跟好的政府機制的制衡以及責任政治的建立致其所對執政者、掌權者的限制。
論總預算審議在野黨不妥適之處
縱然我對於執政黨有許多批評,但談及總預算案風波,我對在野黨的凍結及刪除預算之項目,也有一些認為極不妥適之處。
例如關於行政院台中辦公室,其歷史脈絡其實源於精省之後,台灣省政府之中興新村之公務員歸為行政院各部會之中部辦公室所管轄,後各部會中部辦公室合併成立行政院的中部聯合服務中心。此一歷史定位,攸關台灣省政府,省政府主政時期其效率以及服務備受省民肯定,雖推動精省案,但省政府的各廳處不乏許多優秀公務人員,且其居於中興新村之處台中許久,因此當時有兩個選擇,調往台北行政院及其部會本部,或留在中部辦公室或優退。設立台中辦公室之政策,一來留住許多優秀公務人員,再來也便於中南部民眾關於行政院業務之辦理。
但現在其卻被刪減業務費99%,台中的國民黨立委聲稱,行政院對於中辦的功能性和定位,應該清楚向外界說明,否則有酬庸之疑慮。中辦執行長莊競程表示,影響所及,除了導致業務無法運作,民眾陳情案、地方的災修會勘案件,都將被迫延宕或停擺,甚至辦理護照的業務,也受到影響。在我看來,中辦執行長所言即是,影響到了中南部民眾的權益,導致了區域不平衡,這是不合理的刪減預算。
再者,是在野兩黨對於憲政獨立機關的預算刪減,今年3月18日,監察院副院長李鴻鈞罕見喊話在野黨,表示監院被刪業務費96%,監院幾乎要斷水斷電。理論上,立法院的預算審議,對於憲政獨立機關之預算應表尊重,但立院卻反過來刪除如此多的業務費讓監察院無法為人民服務、無法監督公務員;另外,在野兩黨中,尤其是堅持中山先生五權憲法中國國民黨,真的不會與其政治理念產生衝突嗎?癱瘓憲政機關的行為不正是在毀壞五權憲法嗎?
而論在野黨針對總預算案之凍結及刪減、退回風波,有許多作為受到社會各界質疑。但合理的、認真監督執政的總預算案退回案例,2018年的親民黨團早就示範過了。當年因823水災重創南台灣,政院拿災害未發生前的總預算及前瞻2期特別預算送審,沒有考量現況;當時親民黨也呼籲賴閣揆儘快和在野黨溝通,讓爭議落幕,最後順利解決。
結語:從制度到文化,民主國家都該回到初衷
不論從美國的預算僵局跟政府停擺對比台灣的預算審議僵局,再到細看總預算案風波中,執政與在野的一行一舉,可以得知的是,預算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延伸,沒有一種設計能完全避免僵局,但有效的制度應能保障政府穩定運作,並促使政治責任歸屬清晰化。更重要的,是國民對制度的理解與參與。當公民只看見誰「阻撓」預算,卻不了解其中制度設計與權責歸屬,那麼我們最終將失去的不只是效率,而是整個民主制度的健康與永續。
預算是民主治理的核心部分,不該只是政治舞台上的道具。我們需要更健全的制度設計、更成熟的政治文化,與更積極的公民社會,共同捍衛理性討論與民主政治的基礎。